三、清代中、后期對東南亞的商品化外銷
清代除順治、康熙及雍正年間的部分年代實行了較為嚴格的海禁,其余近兩百年間的海外貿易基本上是開放的。尤其對于南洋地區的歐洲殖民地國家,甚至允許他們到除了廣東之外的閩、浙、江海關貿易。據《道光廈門志》記載: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十八年(1783)、五十一年(1786),嘉慶十二年(1807)、十四年(1809),西班牙的商人萬利落、郎嗎叮、郎安敦、郎萬雷、郎棉一等,就從呂宋(菲律賓)運載大批東南亞特產到廈門貿易,然后從廈門運回包括土茶在內的十余種中國產品到呂宋,使廈門對外貿易進人極盛時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從福建、浙江、江蘇沿海港口出海貿易的商船仍是不少。又據《皇朝政典類纂》記載乾隆二十九年(1764),準“浙、閩各商攜帶土絲及二蠶湖絲往柔佛諸國貿易”。據統計,道光九年(1829),到新加坡貿易的中國商船共9艘,其中從廣州去的1艘,潮州去的2艘,上海去的2艘,廈門去的4艘,共載貨47000擔。道光十年(1830)從廣東的潮州、海康、惠州、徐聞、江門、海南,福建的廈門、青城,浙江的寧波,江蘇的上海、蘇州等地駛往日本、菲律賓群島、蘇祿群島、西里伯群島、馬六甲群島、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新加坡、馬來亞半島、暹羅、安南、柬埔寨等地貿易的中國船只達到222艘。
在如此頻繁的經貿往來中,茶葉以及泡茶所需尤其工夫茶法所需紫砂壺是出口商品的重要部分。陳椽先生在《茶業通史》中分析的個中緣由是“僑銷促進外銷”,即華僑帶動了中國茶葉和茶具在南洋的消費。華僑下南洋的歷史要追溯到元滅南宋后,“一些宋朝遺民以及一些忍受不了異族壓迫的愛國人士和勞動人民紛紛渡海到南洋各國謀生,茶葉也就隨移民在南洋市場大量出現了。”明初鄭和七次率領船隊出使亞非各國,中國與南洋之間的貿易更發達了,茶葉輸出也更多了。經過清初的海禁之后,上文所述福建、廣東商船重新與南洋各國貿易,從中國運出的貨物主要還是陶瓷和茶葉。《茶葉通史》說,當時僑銷茶葉主要以青茶為主,如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緬甸、泰國等地主要消費閩南閩北出產的青茶。而這些青茶沖泡主要是以蓋碗和紫砂壺或潮汕手拉坯為主。所以,隨著茶葉的大量輸出,紫砂壺必然成為重要的附屬品出口到東南亞地區。
這從近年來從南洋打撈上來的多艘沉船的文物上得到了證明。1985年,英裔澳人哈澈(Michael Hatcher)發現1752年(乾隆十六年)在新加坡港東南方沉沒的捷達麥森號(Geldermalson,又稱南京號)并將其打撈,約十件紫砂壺隨即出土。另有1822年1月(道光元年)在南洋沉沒的泰興號(Tek Sing)上出土了更多紫砂壺。這批紫砂壺中數量最多,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工夫茶壺,其形制多達十種,基本涵括了工夫茶壺的主要品類。胎質以朱泥為主,偶有少量紫泥。其藝術特征和閩南地區清墓出土的朱泥壺完全一致,都是宜興產銷,底款多寫刻詩詞,并署“孟臣制“行書陰文款。1845年(道光年間)左右在南洋沉沒的迪沙如號(Desaru)是在19世紀40年代航行于中國與南洋間載運陶瓷貨物和木質商船。
其出水文物也有宜興出產的陶瓷缸甕和紫砂壺,其中有三百把較完整的紫砂壺和更多紫砂殘片,估計當時船上約有八百把紫砂壺,多為紫泥,形制比較單一,絕大部分是較小的梨形壺和直流扁腹壺,底款也多是通行的孟臣款,是較為低端的日用商品壺。從這些出土紫砂壺可以看出,這些砂壺多為南洋華裔需求而制作,為沖泡工夫茶所用,承襲了福建及潮汕茶俗。考慮到清代中國與南洋的經貿關系之密切,商船來往之頻繁,可以想到當時外銷至南洋的紫砂壺數量之多。
另有出口泰國的磨光壺在清中、晚期非常盛行。它是將燒好的成品紫砂壺進行打磨、拋光,加工好的作品光可照人,有“貢局”款和“利興”款,時稱“車光茶壺”,暢銷一時。這些外銷泰國磨光紫砂壺多為泰國富裕人家所制,一般為小圓壺、圓筒壺、水平壺,大多在壺嘴、口鈕、蓋沿等處鑲上金邊或其它金屬,有的配以金屬提梁,部分作品的底款為泰國文字或圖案,整壺顯得珠光寶氣、富貴華麗,充滿異國情趣。“貢局”款銅把軟提梁為這類壺的代表,它是趙松亭于光緒年間所創制。
四、晚清、民國時期通過博覽會對歐美的宣傳營銷
晚清至民國時期,隨著近代中外經貿往來的增加以及國內商業資本的發展,使宜興紫砂業發生了重大而深遠的變化,那就是由傳統的手工作坊式的制作逐步轉變為近代陶瓷商號或公司的批量生產。加之國內興辦實業的風氣影響,這一時期紫砂壺商號和公司如雨后春筍般迅速在無錫、上海乃至國外成立:光緒二十八年(1902),宜興鼎山宕窯戶鮑氏、陳氏合資,在新加坡開設“鼎生福”陶瓷店;公元 1912 年(民國元年) 宜興葛逸云與日本商人和田一雄和田合資在大阪開設陶器店;1903年,宜興鼎蜀鎮窯戶張士清,在杭州開設“張萬隆”陶器店;1905年趙松亭創辦“藝古齋”;1909年,潘寶仁創辦“陽羨紫砂陶業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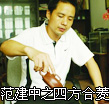

 紫砂壺名家邵順生老師
紫砂壺名家邵順生老師 紫砂壺名家之湯鳴皋
紫砂壺名家之湯鳴皋 高級工藝美術師吳芳娣
高級工藝美術師吳芳娣 高級工藝美術師錢祥芬
高級工藝美術師錢祥芬